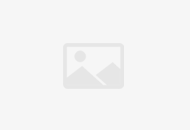曾国藩(1—2)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从他建立功业起始,其社会知名度便与日俱增;及至后来功成名就,社会上关于他的说法已是形形色色;去世以后,关于他的传说和议论更是众说纷纭。这反映了这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体现这种复杂性的材料,除了他本人的海量著作,还散见于他的同时代或随后的公私著作和人们的随笔札记里,须要广泛搜集、细心捡拾,再加以分析,才能将他的真实面目看得稍微清晰一点。
为了让一般读者能够集中读到一些曾国藩的材料,我们从六十余种私人著作中辑录了四百余题涉及曾国藩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的内容,经剪裁厘订,成为这本《曾国藩逸事汇编》。
全书文字内容庞杂,形式多样。为了让读者在阅读时感觉方便一些,兹将全书分成七卷:
前两卷辑录了赵烈文、郭嵩焘、李兴锐、张文虎和王闿运共五人日记中与曾国藩有关的文字。这五人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或先或后、或长期或短暂地充当过曾氏的人物,有条件直接跟曾氏打交道,耳闻目睹,随手作记。多是那个年代的目击记录。
卷一的内容辑自如今存世的赵烈文两种日记。赵氏在曾幕期间,与曾朝夕相处,他笔头勤快,逐日详记,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历史现场实录。我们从赵氏《落花春雨巢日记》中摘录了他加入曾幕的最初历程,又从《能静居日记》中摘录了同治二年(3)作者再入曾幕,直到同治十一年(2)曾氏去世的有关内容。其间赵氏在曾幕经历和见证了诸多历史事件,天天与曾氏作倾心交谈,有时甚至一天谈几次。赵烈文将双方谈话都做了详细记录。这些谈话,双方都很随意,尤其是曾氏的谈话,比其家书更坦率,接触时政更多,从而更直白地坦露了曾氏心迹。曾氏许多对时政的观点,在他存世的文字中往往看不到,赵氏留下的谈话记录里却有大量记录。可以说,这部分记录对于了解曾氏的真实思想、认识曾氏的另一面,是极为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是对现存曾氏全集的重要补充。
赵氏文笔细腻,下笔不忘记留下细节,文章现场感极强。在湘军围攻天京时,赵氏还兼任曾国荃的机要幕客,对攻城部署多所贡献,这都不是主要。重要的是对湘军攻陷天京后,滥杀无辜的残忍、劫掠财物之贪婪等情形,记载极详;对起义领袖骄奢生活的暴露,也是真实具体。等等这些,均是现场实录。笔者过去读关于这段历史的相关著作,常常担心作者预设立场,对他们的书写常常持怀疑、保留态度。读了赵氏的文字,终于相信这段历史确实有过如此残酷血腥的一页,胜利者确实是如此贪婪和毒辣!起义领袖的实际作为,跟心目中设想的形象之距离又是何其遥远!因此,笔者接触这些文字的时候,不禁深深佩服赵烈文的诚实!事件的本体属于曾国藩事功的范畴,不可不录。
卷二的内容辑自郭嵩焘、李兴锐、张文虎、王闿运的日记。郭氏对曾国藩极为尊重,曾氏出山组建湘军,就有郭的功劳;郭对曾认识深刻,见解超群,始终支持曾的作为;一直到曾去世后还积极参与曾后事的料理,在筹建曾祠的过程中出力尤多。郭在日记中发泄了对曾国荃,尤其是对曾纪泽的不满,当然有诸多具体原因,也写下了对曾纪泽的外交活动的不同看法。曾纪泽是他外交职位的继任者,是不是有被“取而代之”的心理影响?留待研究者去思考吧!郭氏是曾国藩积极形象的维护者,日记中对与曾关系相左的左宗棠表现出十分不屑,直到左死,还在日记中说“且伤且感”之类的话;郭也看不起王闿运的学问,对王写的《湘军志》坚决反对,鼓励朱克敬著书跟王书唱反调,在光绪八年五月初二的日记中即透露过朱氏“以所撰《拟湘军志》呈阅曾沅浦”的消息。
李兴锐以务实著称,选取的这部分内容主要记叙了作者与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经过。日记披露了处理过程中颇为罕见的情形:刚开始李兴锐等属员甚是高调,建议曾国藩起用彭玉麟等湘军老将以筹战守,但曾氏却冷静得多,认为“未可轻率开衅”;经朝廷认可,曾国藩、李鸿章做了妥协处理,但在处理过程中做了手脚,如修改天津府县的“招供”,以减轻府县“罪责”;曾氏还亲审“罪犯”,“审问至夜,仅有两人众供确凿,本人则尚未承认也”。既得不到实供,又要向上交差,曾氏无奈斩杀十五人,以息洋人之怒,事后又每人抚恤白银五百两。如此莫可奈何的处理,当然得不到时人的谅解。曾氏后来亦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表达自己的良心责备。然而郭意城(郭嵩焘大弟)对此表示了足够的理解,他在为朱克敬《瞑庵杂识》关于此案的记叙作的签正说:“曾文正办理此案,明知必遭时俗指斥,而考之事实,准之情理,势不得不出于此。事外论人,原多任意高下,及至中外交涉,则是非曲直,尤不能适得其平。此则叙述,似但沿世俗之论,未尽合当日情事。”关于本案斩杀民人数目,按朱克敬的说法,曾氏原拟据洋人死数,对等杀二十一人偿命,未料俄使可能动了恻隐之心,认为当时是民众同法国人闹矛盾,“杀俄人,误也;今又无罪以偿,是重误也。请毋偿俄国六人”,乃斩十五人以徇(李兴锐同治九年九月廿四日日记称十六人)。朱克敬是郭家兄弟的密友,消息来源直接,此说当不至离谱。
张文虎是曾国藩晚年在金陵刻书的实际操办者,二人交集甚多,张在日记中多有记述。我们辑录的内容,主要就是记录二人在校勘刻印活动中的交流,其中不乏曾氏的具体指导和真知灼见;又有关于曾氏处理过的著名事件(如刺马案、教案等)之因由的记叙,以及当年南京被攻克后的场景、后来渐趋恢复繁华的所见。结合前面赵烈文所记,更能帮助读者寻求历史真相。曾国藩和张文虎等人之间就刻书、校书之事应该多有书信往来,岳麓新版曾氏全集发稿前未觅得一通,足见搜集书信是何等艰难的事。
王闿运在曾幕时间较短,而且那段时间的日记没能保存下来。在现存《湘绮楼日记》中,王氏记下了曾国藩晚年时二人的交集,对曾氏去世后也有不少点滴印象记录,甚至王氏自己到了晚年还数次在梦中与曾氏有过相会,可见印象之深。曾国藩和王闿运毕竟不是一路人物,二人所崇尚的并不一致,处世态度当然不同,在极具私密性的日记里,王氏对曾国藩的不满甚至不认同便自然流露出来了。而且在曾氏死后王还写了一本令曾家不满的《湘军志》,王氏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因其直言和相讥,引得曾国荃愤怒不已、郭嵩焘激烈反对,就不奇怪了。此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王氏甚至对劝他将书版交郭嵩焘处理的人大发牢骚:“吾以直笔非私家所宜……外人既未出赀属我刻,而来索版,是无礼也。”一番慷慨陈辞之后,王氏大约是知道众怒难犯,过了三天,便赌气将《湘军志》版片和成书一起交郭烧毁(王日记光绪八年正月十七、二十日)。王氏对此事一直难以释怀,此后亦与郭疏于交往。事隔半年,郭嵩焘登门拜访,王仍托辞不见(八月十日日记);又闻“沅浦褫职,季高失势,湘人顿为笑柄”,幸灾乐祸之情,溢于笔端(八月十一日日记)。此类故实,王的日记中均有所记。
曾国藩同时代人士在日记中记载曾氏逸事的尚有不少。有的记叙过于简略,有的事件过于分散,本书取赵、郭、李、张、王五人的日记为代表,用以显示晚清日记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多么丰富的矿藏。
卷三辑录曾国藩同时代人士的笔记撰著。这些人士多数见过曾氏,有的与曾关系还很密切,但少数几位则不一定见过。他们的记叙不是像前面几位日记作者那样的现场即时实录,姑且把它们视为“追记”,其排列按作者出生年代为序。毛祥麟《三略汇编》全录了经曾国藩(包括赵烈文)删改的李秀成供词。如今李秀成供词真迹已经公开影印出版,经改窜的文本却难得一见了,本卷特予录入,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对观。如果读者还想进一步了解当年改窜李秀成供词的过程,不妨去查查处置李秀成的那些天(同治三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曾、赵二人的日记,也是很有意思的。
卷四、卷五辑录自曾国藩在世时尚未成年或曾氏去世以后出生的人士的撰著。他们关于曾氏的写作有回望的性质,其材料来源,或得之耳食,或抄撮改编前人作品,或索性对已见材料加以发挥,总之是隔了一层。但各有特点,值得曾氏逸事者一读。由于有些材料被重复利用,只要有自身特色,不是直接一字不改的抄撮,本书尽量保留,但在篇末注以“相关链接”,以利读者分析。
清末民初由于印刷业的发达,报刊的兴起,催生了一批专事搜辑民间逸事、朝野旧闻的作者,有的还以排比考订这些历史碎片作为研究历史的手段,并卓然成家。但终究没有脱离札记和随笔的模式。卷六和卷七便是从民国时期六位掌故大家的八部集成式作品集里选取有关曾国藩的篇什,汰除重复,各依原书归属而成独立单位。六位作者中徐凌霄、徐一士兄弟最为突出,他们运用材料严肃认真,例如本书辑录的《靖港之役与〈感旧图〉》等篇用力甚勤;柴小梵、黄濬等作者广征博引,见闻独到,他们撰著中的相关内容便成为必然之选。
编者早就有选辑曾氏逸事成书的愿望,但实际动起手来,其工作的繁复程度远非原设想的剪刀加糨糊那么简单。同一条内容相同或相似的材料,被不同的作者引用,被他们朝不同的方向发挥,面目便大不相同。然而这种发挥都各有选取的价值,怎么办?只好忍痛割爱一些,保留一些。读者今天在书里读到的,可能仍有少量的某种程度的似曾相识,就表现了编者面对上述情形的无可奈何。曾氏还是公认的联语高手。本书中偶有重复出现者,那并非编者失察,而是因其个别字词相互略有不同,有意留下作为校勘材料。读者如觉不妥,敬祈谅之。
关于本书的编辑规则,已见于卷首凡例,此处不再复述。
当然,散见于晚清笔记中的曾氏逸事资料还可以找出很多,但要编出一部曾氏逸事大全,笔者目前尚无力做到。因为晚清史料浩如烟海,爬梳剔抉,阅读量太大;见面也不容易,许多远远够不上珍本善本资格的书,仅仅以其线装,如今还躺在公众图书馆的书库里中饱蠹鱼。笔者有幸充当过几种入藏已有数十年的木刻本的首位借阅者,且不说索书时间之长,光是在戴着防毒口罩和薄膜手套、年纪肯定小我几轮的工作人员那冷漠的炯炯目光注视下,翻找着有关篇什,就感觉别扭。那注视的目光仿佛把我看成了高超的魔术师,有把书本在他眼皮底下变走的本领。此刻我不忍心使用另一个词,但今后继续多买书的念头更难消退了——不过怎么买得过图书馆呢?!
曾经有朋友向笔者提议,把材料逐题打散,然后按曾氏生平顺序排列组合。这个想法当然很好,但笔者尚不具备这个胆量,因为材料参差错落,真伪难辨。重加考订,那是撰写专著的做法,把读者的思索辨析环节通通代劳了,似无必要。本书作为笔记类型的传记资料,编者原拟按各自主题做个索引。但事到临头却感觉无从下手,只好让它以传统的笔记面目示人。限于篇幅,编者对人名未作笺释。考虑到本书不是一般通俗读物,读者对晚清历史具有一定知识储备,阅读时不致有太大问题。
八十六岁高龄的锺叔河老先生支持编者做这个工作,欣然赐予题记,以为鼓励,为本书面世,大壮行色,编者殊觉光荣。
期待着各路高明的指点赐教。
朱树人
本文为岳麓书社《曾国藩逸事汇编》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