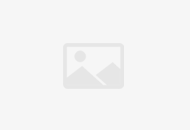知青生活永远难忘,记得那是在1975年8月的一个星期日。早饭后,我和同宿舍的上海知青小陆带上了水壶、干粮,背上一枝弹匣已压满子弹的"五六"式冲锋枪(那年我被抽调在牡丹江市郊区当武装基干民兵),顺便领着一黄一黑两只半大不小的狗(我们知青喂养的小狗),去林场石峰沟一带的山区狩猎。
其实也谈不上是狩猎,我们根本就没这方面的经验,纯粹就是仗着有杆枪去山上瞎转转罢了。刚开始我俩还是精神抖擞,浑身是劲,那两只狗也是蹿前跑后的煞是欢快。翻过几座山头已经过了大半天,干粮已吃完,水也喝尽了,俩人累得快趴下了,但还是什么也没遇上。原先那两只前呼后拥,边跑边撒欢的主儿,此时也只有耷拉着脑袋、伸出舌头喘息的份了。
又翻过一座山头,山顶的大树上传来一阵老鸹子(乌鸦)的噪呱声,抬头望去,一棵大杨树上停留着几只硕大的老鸹子。唉,在山上转了大半天还没动过枪呢,于是决定拿这些乌鸦来出气。我端起冲锋枪,打开保险对着树顶上的乌鸦来了几个点射"呯?""呯?",枪声过后那些老鸹子毫发无损地飞走了。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带去的那只黑狗听见枪响后竟被吓得夹着尾巴躲在我俩身后吱吱呜呜的不敢动弹,而那只黄狗更是撒腿就跑,一溜烟的就不知去向了。我和小陆在山上一个劲地呼唤着那只黄狗,几个时辰后还是不见黄狗的踪影。
返回吧,我俩垂头丧气地从山上往回走,黑狗由于受到惊吓已经失去原有那股撒欢劲了。我俩挪着疲惫的双腿艰难地回到宿舍,还没顾得在炕上歇一会,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出现在我俩眼前。在山上找了半天没找到的黄狗,居然已经躺在宿舍门外的狗窝里睡大觉了,气得小陆撅了根柳条子把黄狗拖出狗窝狠狠抽了几下。
这两只被视为没有培养前途的狗狗最后的结局是悲惨的,几个月后那只被养大的黑狗用来与当地的朝鲜族老乡换了60斤大米,那只黄狗则被我们这些知青当下酒菜了。
需要说明的是:林场附近的生产队有不少朝鲜族住户,他们有吃狗肉的嗜好。曾有朝鲜族青年多次来我们宿舍交涉:要么用大米来换黄狗,要么他们迟早要来偷走那只黄狗。后来发生的宰杀黄狗事件纯属无奈之举。
猎 趣:
那一年的深秋,我背着一杆老式的"七九"步枪,带着邻居家的一只大黄狗(没训练过的草狗),去灯笼树沟一带遛套子和狩猎。
走着走着,在一条小河沟通往半山腰去的树林里,大黄狗忽然从前面斜坡上呼哧呼哧快速朝我跑来,然后一头躲在我的身后吱吱呜呜的浑身哆嗦着,当时我就料定大黄狗可能是遇到了什么大家伙了。
我屏息仔细倾听和观察坡上的动静,在树叶和茅草的遮挡下什么也没看到,但已经能听见坡上林间传来哧啦、哧啦的声响。我端着已经顶上火的枪,轻轻地安抚着大黄狗让它继续上去,大黄在我的指引下狂吠几声又往坡上跑去。可能也就二十多秒时间(我跟在后面还没走几步呢),大黄犬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我的方向逃了过来,并往我胯下钻,差点把我绊倒在山坡上。
我定神抬头一瞧,天哪!一只大黑瞎子(黑熊)紧撵着狗从坡上冲了下来。与黑瞎子这么近距离的相遇,在我多年的狩猎生涯中还是第一次。出枪已经来不及了,我赶紧闪躲在一棵大椴树后面,顺手掏出一把防身用的匕首准备放手一搏了。好在那黑熊在大树后面没收住脚,沿着坡道一直往下扑,然后大大咧咧蹿进沟对面的林子里了。
啊哟,一身冷汗的我一屁股坐在大树底下,一边喘息着一边诅咒着那只该死的大黄狗,并发誓今后再去狩猎绝对不会带这种没经过训练的草狗。
这是根据原牡丹江市林业局东村林场检尺员刘明久师傅亲身的生活经历撰写的,他说一只训练有素的猎犬应该是紧紧圈住猎物扯咬或围绕猎物狂吠等候主人前去猎杀。
夜袭毛豆地:
1973年入冬前我们搬进了林场为上海知青新盖的宿舍,那是一排崭新的坐北朝南的砖瓦结构平房。宿舍门前有一条行人踩出的小路(常年踩踏后形成的一条便捷小道),往东直通百米开外的东村林场大桥,小路两侧约有三、四十亩耕地。
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且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五谷不分的,所以对这片紧挨着我们宿舍的农田究竟种了哪些农作物都是傻傻分不清楚的。
夏令季节,我们几乎都会在下班后沿着门前的小路去大桥边洗衣、搓澡的(桥下是山上泉水汇集而成的一条小溪)。
也不知哪一天,我们忽然发现小路边农田里齐腰高的农作物上挂满了毛绒绒的豆荚,请教了林场的师傅们才知道这片农田种植的是大豆。记不清是谁顺手摘下了几个豆荚,我仔细辨认后心中暗暗窃喜,天哪!这不就是上海菜场经常能看见而且是当蔬菜卖的毛豆吗。
当晚我们几个男生就壮着胆子去地里拔回了一捆结满豆荚的大豆青棵,关上宿舍大门,摘豆荚、洗豆荚、煮豆荚。然后围坐在炕上品尝那一大盆鲜美无比的毛豆,与食堂饭菜相比,这盐水煮毛豆简直就是美味了。这天大家都睡得很晚,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难得一见的惬意笑容。
第二天,宿舍门外农田种的是毛豆这个消息在知青群里悄悄地传开了,大家都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个个都摩拳擦掌,盼着夜色快快降临。晚饭后大伙们都忙开了,有把铝制脸盆清洗干净的(权当煮毛豆的锅使用)、有负责把水缸挑满的、有往煤油炉里添加柴油的、还有出各种主意如何去拔毛豆的……。
接连几个晚上,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年轻人都会悄悄地潜入大豆地里,你一捆、我一搂,肩扛怀抱的逃回宿舍……。几天下来,经过我们轮番袭击后,那片地里的大豆已经被蚕食的东缺一垄,西少一块的了。不久之后东窗事发,家属生产队的边龙天队长告诫我们:今后不能再这么搞,先前的事就不追究了。自那以后我们再没侵犯过那块田地里的农作物,第二年起,那片大豆地开始改种大白菜了。
现在回想起当年所做的这些事仍感到脸红,我们夜袭毛豆地,说轻点是年轻人为了解馋干了件荒唐事,说的严重点就是偷盗林场的集体财产。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要感谢当年的东村林场领导和家属生产队长能宽容犯了错的上海知青们。
战花蛇:
四月末的牡丹江,冰封半年之久的黑土地和广袤山林已经完全融化,呈现出一片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景象。
这天,我们五、六个知青被安排去双桥一带的山坡上刨穴(在林木稀少的山坡上等距离刨出一个直径约50厘米的小坑,第二年的春天可以栽植树苗)。林场的女青年小宋驾驶一辆手扶拖拉机负责接送我们上下班,个子高高的小宋熟练地打着了拖拉机发动机,坐在拖拉机的驾驶座上牵着载有我们的小挂车"突突突"地驶离场部。
说起来也真的很奇怪,我们这些男知青虽然出生在上海,长在大城市。也不知道为什么,到林场工作后个个胆大的出奇,一般情况下,一米左右的遛子(蛇,也称長虫),谁见了都敢抓在手里玩耍,自然也包括我了。胆子最大的是夏老师(同去的上海知青,后被调去林业子弟学校任教体育),他甚至能每每抓到腹蛇之后就直接扒去蛇皮,取出蛇胆生吞下肚,说是有明目清肝的作用。其操作手法的熟练程度令人咋舌,我可从来没有胆量去尝试。
迎着和煦的阳光,我们有说有笑一路颠簸着驶向作业的山区……"嘎吱"一声,手扶拖拉机紧急刹车停在被称为双桥的小桥头上。"大遛子"小宋姑娘惊恐地大声叫唤!哪有什么遛子啊?挂车上的我和知青小詹都有高度的近视(平时都不戴眼镜),"在那,那不是吗”小宋还没缓过神来。那不是一堆牛粪吗,我和小詹眯着眼睛朝小宋所指的方向看,心里嘀咕着。向桥上望去,只瞅见大约离拖拉机三、四十米远的桥面上有一大坨扁扁圆圆的、黑呼呼的东西,"那就是一堆牛粪"小詹用沪语自言自语的说。“是遛子,是大遛子,我可不敢驾拖拉机过去"小宋带着哭腔加重了语气。我和小詹只得跳下拖挂车,每人提着一把锄镐(刨地用的工具),一溜小跑朝那形似一堆牛粪的玩意奔去。
大约离那堆"牛粪”三米远时我俩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这下看清了,果然是一条蛇,一条大约比镐把还粗一些的大蛇。只见那条大蛇懒洋洋地一动不动盘卧在桥面铺设的木板上,可能是刚出洞不久,正在接受阳光洗礼的它竟然无视我们的到来。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条死蛇,凑上前用锄镐去扒拉它一下,仍然是懒得理你的模样,只见它慢慢地将蛇身舒展开来,慢慢的将头朝桥面木板缝里游去。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乖乖!一条手腕粗细约2米长的大家伙,黑一段白一段的花纹布满整条蛇身(这是我第一次在林场山区看到有这种花纹的蛇,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大花蛇旁若无人地将身子慢慢往桥缝里挤,说时迟那时快,不服输的小詹扔掉手中工具,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还没来得及完全挤进桥缝的半截蛇身的尾巴使劲往外拽。说实话,看到这么大的蛇我也有些胆怯了,"你快过来帮忙拽呀“,我站在原地没挪步。脸涨得通红的小詹使出了吃奶劲儿玩命地往外拽,拽出一米长了,拽出一米半长了,再使一下劲整条蛇全拽出来了。
刚开始,被拽出来的大花蛇脑袋还耷拉在桥面地板上,只是扭动身子想挣脱被拽住的蛇尾,小詹高高举起的双手紧攥着蛇尾不放。不一会儿花蛇抬起头身子呈U字形凌空游向小战,小詹攥着蛇尾使劲抖动蛇身(蛇小的话,拎住蛇尾巴抖动,蛇的脊椎骨就会暂时被松散开而无法抬起头来)。无奈这条蛇实在太大了,蛇的长度超过小战的身高,根本就没法拎直了来抖动蛇身。眼见那吐着信子的蛇头快要触碰到自己脸颊时,小詹松手扔下了大花蛇。被摔疼了的大蛇迅速朝拖拉机方向游去,在伴有小宋姑娘的尖叫声中,我和小詹左右开弓用锄镐将大花蛇斩成数断。
哦,若不是小宋姑娘发出惊叫声的话,我们绝对不会斩杀那条大花蛇的,实属无奈之举。
生擒野猪记:
时间是在1976年的深秋,已经进入采伐季节了,记得这年是在灯笼树沟一带进行采伐作业。
那天午饭后我在帐篷外的一块空地上翻晒松籽(自己和同伴攀树采摘的)。只见曲老四(曲兆顺师傅)兴冲冲地从林间小道疾步走向我们居住的帐篷,在帐帘外轻声呼唤他的五弟曲兆胜(曲家兄弟五人,个个身手了得,下套子、遛套子、抓野鸡、逮兔子样样精通)。
他俩在帐篷外的交谈声顺风刮进了我的耳朵,大意是:曲老四前几天在离帐篷约三里路的后山下了套子(朝北的山坡,一般都是柞树林子),刚才去遛套子时发现套着一只大野牯猪(大公猪)。下的是活套,猪脑袋钻进去后一半拉已经滑套了,钢丝绳一边紧勒在猪的左獠牙上,另一边滑出獠牙死死勒住猪的右边拱鼻肉内。由于是活套(就是一种将钢丝绳固定在一根长三米左右的坑木上,坑木在林子里被拖着走的话,会时常横在或卡在两棵树木之间而动弹不得),那只仍活着的野猪看见曲老四后就一个劲乱蹿,极有可能会被勒去半个猪鼻而逃之夭夭。
他让曲老五下山去场部取枪来收拾那只野猪,老五利索地推了辆自行车沿着下山公路飞速离去。大约两个小时左右,身背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的曲老五气喘吁吁地走进了帐篷。我们一行(我和另外一个知青纯粹是去瞧热闹的)约六、七个人带着枪和斧子,麻袋,绳子等家什,由曲老四领着朝目的地进发。
曲师傅带着大家翻过一座山梁来到北坡,大伙跟着他蹑手蹑脚慢慢地向下移动着脚步……。忽然,曲师傅大手一挥,给大家发出了停止前行的信号。可能是那头野猪也已察觉到有人在靠近它,只听见忽啦啦的一阵声响,山坡上厚厚的落叶像被大风刮过似的飞扬了起来。哇,看见了!一头灰黑色的大野猪被钢丝绳斜勒住獠牙和半拉猪拱鼻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钢丝绳深深地嵌顿在猪拱鼻里。又是忽啦一声,那头野猪猛地朝我们站立的方向一蹿,因被钢丝绳拖着的坑木横在两棵柞树之间而无法接近我们。
"不要靠近了"曲师傅指示大家距野猪约30米处呈扇形席地而坐,呵呵,在山上坐在松软松软的落叶上等着亲眼目睹曲家兄弟擒住那头野猪绝对是一种感观上的享受。这时曲老五端着枪往前走了十来步,大约离野猪二十米远时他用半跪的姿势举枪瞄准目标。可能是经过长时间的挣扎,那头野猪巳经没有原来的疯狂劲了,站在那里恶狠狠的看着我们,嘴里只有哼哼的份了。
"呯"第一声枪响后,没有动静(子弹从厚厚的鬃毛上蹭飞过去),野猪转过身来,两只小不点的眼睛露出了凶光,喉管里发出了更吓人的哼哼声。"呯"第二发子弹不偏不倚的从野猪右肩胛中钻入胸膛,扑腾一声,野猪一个趔趄前腿跪地而卧,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吼叫声。"呯"又补了一枪,姿势还是原来的样子,吼叫声却渐渐的低沉下来了。我们站起身慢慢围过去,一个叫付德连的青年人拎着一把大斧子走到还在作垂死挣扎的野猪跟前,用斧背对着野猪脑袋使劲砸了几下。那头可怜的野猪带着钢丝套瘫软在山坡上了,足足有三百来斤的大野猪就这么毙命了。
"快放骚,快放骚”曲家兄弟抽出锋利无比的腰刀,动作相当熟练的割除了大公猪的外生殖器(据说公猪不这么处理的话,猪肉会有一股膻味)。砍了一棵柞树杆后,大伙七手八脚把那头野猪抬回采伐工段营地。后来那头野猪大部分归曲家兄弟了,采伐工段伙房留了些肉,第二天全工段几十号人美美的吃了顿用野猪肉制作的大餐。
知青生活往事,我们永远难忘的记忆。
原牡丹江市林业局东村林场 上海知青 郁以凡(老知青家园荐稿)